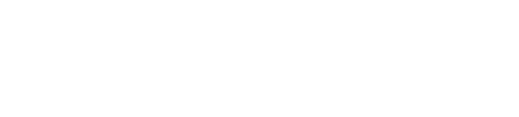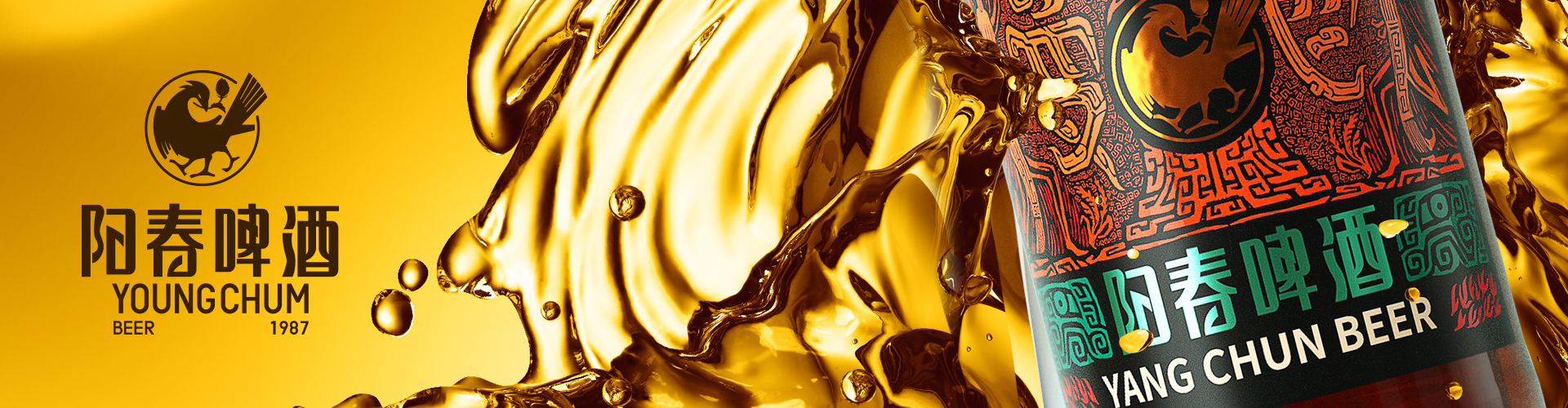啤酒知識 


早些時候,英國考古學家和中世紀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朗蘭茲出版了一本引人入勝的書:《精釀啤酒:傳統工藝的起源和真正意義的探究》。這本書的目的是重新找回“手工藝”的含義,因為它在成為營銷口號或精品店出售的昂貴商品之前就已存在。朗蘭茲以學者的眼光回顧過去,挖掘這個詞的原始含義,看看它如何豐富我們當前的制造方法,在一個有機器或應用程序為我們做事的世界里。
我不想引發任何爭論,但這是事實:工藝已經變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越來越難以準確地表述一個足以滿足每個人的定義。當然,這與制作有關,而且制作具有可感知的真實性:手工,充滿愛;來自原始的天然材料;達到所需的標準。但它并不一定會產生一個對象。最近對精釀啤酒的熱潮意味著我們可以消費精釀啤酒,但實際上卻一無所獲。在藝術世界中,它既可以是一種方法論過程,也可以是一種概念工具。在奢侈品的世界里,一種保證是你正在獲得金錢能買到的最好的產品……但即使在今天“工藝”這個詞的廣泛使用中,它與“工藝”的定義也只有最微弱的重疊。一千多年前它第一次出現在書面英語中時就已經出現了。
朗蘭茲從語言學、經驗和哲學角度進行探索,翻轉這個主題,考慮它的歷史和與語言的聯系、物理步驟以及與大師的交談。他還參與制作過程。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致力于介紹不同類型的傳統工藝,例如蓋屋頂。朗蘭茲使用他的所有三種研究模式來考慮茅草(他告訴我們這個詞來自古英語t?c,屋頂,但得出的結論是這并沒有多少智慧),并讓讀者對一個簡單的物體有比他們更深刻的理解。曾經想象過。
這本書從朗蘭茲第一次偶然涉足手工藝開始,當時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第一次拿起了一把舊鐮刀。一位路過的司機告訴他如何正確使用它,出于好奇,他整個夏天都繼續使用它。當鐮刀不再是概念性的時候,他學到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花園的形狀也發生了變化;直線被寬闊的曲線所取代,角落變得圓潤。” 這種非概念性的洞察力使他對“工藝”的古代含義以及現代人可以從中獲得什么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克雷夫特意味著什么
Cr?ft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詞,朗蘭茲研究了它的使用方式。“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含義是在知識、能力和一種學習的背景下的技能的力量。此外,一種心理技能的感覺——優點、天賦或卓越——出現的次數與身體技能感。” 后來,他總結了自己對這個詞的理解:
“手、眼、頭、心、身的協調讓我們對世界的物質性有了有意義的理解。”
這個概念在中世紀并沒有被描述或定義——為什么會這樣呢?在前工業時代,一切都是手工制品。這個術語幾乎以負空間的形式存在,只有當我們能夠在機器上批量生產東西時,它才有意義。然后,了解人類如何手工制作東西以及當我們將它們交給機器時會丟失什么就變得很有價值。
對于朗蘭茲來說,技藝是存在于身體中的知識。當我們重復做一件事時,我們就會開始掌握;我們的身體經過一千次重復之后,知道如何做一件事。這就是Cr?ft的中心點:智慧和技能來自工匠的身心,而不是機器。他必須在這里做一些拆包工作。人類非常聰明,我們制造機器已有數千年歷史。其中一些使工藝變得更容易,但不會妨礙身體的智慧(例如圍繞重物移動的機器);其他人則這樣做。他用一個最英國的例子解釋了這句話的重要性:
修剪樹籬的工藝可以分為三個物理功能。第一是權力的運用。第二個是動覺敏感性,它使我們能夠將我們的身體、手臂和手塑造成一個位置,從而使我們能夠實現第三個,即切割的動作……我不認為使用電動綠籬機的修剪師是真正的工匠的理由很簡單,即該工具削弱了與他們正在工作的實體的材料屬性的接觸程度。
工具和機器之間的區別并不是偶然的,工具讓工匠能夠運用力量和“動覺敏感性”,而機器則消除了這些能力和“動覺敏感性”,而這正是工藝的本質。
精釀啤酒
當然,我讀這本書有一個特定的議程:我想知道朗蘭茲的觀點如何幫助我理解工業啤酒和精釀啤酒之間的區別——如果有的話。(除了我上面引用的提及之外,他在書中沒有考慮啤酒。)這曾經看起來如此明顯,但我們越仔細研究它,我們就越會被無關的考慮所困惑。

啤酒并不是最容易考慮的工藝,因為它幾乎從一開始就利用了機器。它是一門復合工藝,從田間到杯子,要經過多次操作,而不是像用鐮刀割干草那樣簡單。一路上,使用各種工具和機器來移動重型原料,操縱和組合它們。對工藝的規定性定義只會讓我們陷入定義允許的做法的泥潭。如果不使用機器,就不可能以商業規模生產啤酒。問題是:這些機器什么時候才能將工藝從釀造中移除?
工藝存在于工匠的身體和智慧中,而不是機器中。一些設備實際上為啤酒釀造商投入了更多的能量——例如,漩渦使啤酒釀造商能夠向啤酒中注入一定劑量的啤酒花。但每次啤酒廠將部分流程自動化時,它都會將啤酒制造商手中的智慧轉移到機器中。機器精確且一致地做事,但每次我們用它們代替物理行為時,我們就離流程越來越遠。這些小讓步的增加使釀造行為從主要由啤酒廠定義轉變為由啤酒廠定義。智慧從人轉移到機器。
我采訪了數百家啤酒廠,其中許多人是在參觀他們的啤酒廠時采訪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磨練了自己的技藝數年或數十年。他們已經生產了數千批啤酒。更資深的釀酒師——John Keelings(Fuller's)、Hans-Peter Drexlers(Schneider)和 Jean Van Roys(Cantillon)——所傳達的東西不僅僅是深厚的經驗。他們暗示著他們對啤酒的了解,但他們并不總是能表達出來;這是他們骨子里的東西。當您與曾在自動化程度不高的啤酒廠工作過的經驗豐富的釀酒師交談時,您會聽到他們暗示“工藝”。
他們經常訴諸類比、隱喻或詩意的語言,而這正是最好的啤酒寫作的素材。然而,總有一些遙不可及的事情。我最生動的記憶之一是與釀酒師 Adam Bro? 一起參觀布德瓦爾啤酒廠。即使對于捷克共和國來說,布德瓦啤酒也是一種不尋常的啤酒。一次又一次,我們會討論啤酒廠的一個特質,布羅茲就會求助于科學。該啤酒廠做了很多研究,他用研究來證實他們的方法。如果我輕輕地指出發現不同結果的研究,他會微笑;他認識他們所有人。但布德瓦爾幾十年來一直使用的做法,以及布羅茲學到的、現在正在實踐的做法,對他來說有著直觀的意義。這些過程和啤酒是密不可分的;在布羅茲采取的每一個行動中,他都能感受到啤酒的效果。工藝品。
我將用朗蘭茲的另一段話以及關于它如何應用于啤酒的評論來結束這篇很長的文章。他觀察到:
在藝術世界中,自由美可能會因對功能的依賴而受到污染:形式和外觀應始終被視為純粹美學的一部分。但我會判斷一個好的鉤子的鍛造,不是看它的美觀程度,而是看它的形狀與我用過的其他鉤子的形狀有多接近。它的吸引力——以及它的美麗——取決于它作為鉤子的功能。我們越來越與依賴美作斗爭,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放置或使用功能性的工藝品。我們不知道用什么來衡量這種美麗。它依賴什么?我們對溫暖毯子的真正價值感到掙扎,因為我們的中央供暖系統永遠不允許我們變得足夠冷。
啤酒不像鉤子或毯子那樣是一種功能性商品。然而,在每種類型的啤酒中都蘊藏著巨大的人性財富——我們的農業資源、我們的喜好、我們的飲酒方式、我們的歷史、戰爭和饑荒留下的傷痕、法律的殘余,以及釀酒師為之奮斗的所有方式。幾代人都根據這些現實調整了他們的工藝。當一位工匠大師(釀酒師)在她熟悉的啤酒廠釀造第一千次或第一萬次啤酒時,智慧就會傳承下去。當同一位釀酒師決定將這種智慧——不僅是在釀造過程中,還有人們如何消費和享受她的作品的知識——投入到一種新啤酒中時,這種智慧、這種工藝就會得到發揚光大。
在另一個極端,高度工業化的過程看起來與此相反。新啤酒的靈感不是來自釀酒商,而是來自營銷團隊。它的輪廓是由從釀造行為(某些風味或市場利基)中去除的抽象概念定義的。這種啤酒被設計為在只能以有限的方式釀造啤酒的機器上釀造——新啤酒必須遵循機器的限制。啤酒的參數被輸入計算機,新口味的啤酒從另一端出現,無需參考一長串的人工輸入。這顯然不是什么技巧。
大多數啤酒廠位于連續體的這兩點之間。使用工藝邏輯,很容易想象,一家公司擁有的大型啤酒廠比一家缺乏經驗的家庭釀酒師經營的小啤酒廠更接近真正的工藝。但在每種情況下,它都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方式來思考啤酒廠,而不是規模、所有權結構或其他常見指標。我總是對最新的發明或趨勢感興趣,但我真正喜歡的啤酒不僅僅是聰明的產物。但釀酒大師的產品,充滿了更深層次的工藝智慧,通常更令人滿意。也許我可以寫一篇關于我們如何 更具體地使用這個概念來思考啤酒的文章,但現在就足夠了。